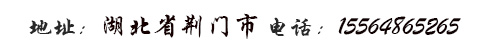草木缘情
|
我们班维护的岗位有一些是在厂外的山坡上,走过去得花大半个小时。山上有各种树,比如桑树,到了夏初,树上挂着星星点点黑紫的小桑葚,这些桑葚是山上的麻雀吃过一轮的,我们在树下仰着头寻着熟透了的吃,比市场上买的多一点雀跃的心情,仿佛更好吃一点似的。那里还有山楂树,杏树,柿子树,花椒树…… 曾经有两棵无花果树种在岗位操作室的门口两边,叶子繁盛浓密,绿荫如盖。无花果的结果期很长,横跨整个盛夏,我们只要在门口停步抬头张望,有人就会到屋后的院子里寻出来一个长竹竿,把果子拧下来递到手里。无花果绿莹莹的果皮,红殷殷的果肉,像是盛着蜜一般浓厚的甜。我们会在树下聊几句闲天,关于天气,工龄,退休,甚至是老家何处,两棵果树缘何而来。时间那会儿像是忽然变慢了,慢到一回头能看见时间真快。隔年忽然发现四处草木茂盛,唯独两棵无花果树寂寂无声,岗位上的人说去年冬天太冷,无花果树没抗过来冻死了,这也才发现聊过天的人已退休了两个。 那年最冷寒流零下二十多度,让人记忆深刻。我们班里整宿地在现场忙,用蒸汽带一台表一台表地吹开冻住的管线,隔壁班长在现场时间最长,脸竟冻到微微发肿青紫。装置安然无恙地顺利运行下去,想不到这样粗壮茂盛的两棵大树竟再也不能发芽。最近听说隔壁班的班长在家里病休了一阵子了,咋一听觉得诧异,因为那么粗犷的一个人,一副生猛不忌的样子,像是水浒传里的绿林好汉。如今竟休了病假,中间像是漏掉了什么环节对接不起来。 那个冬天死的不仅仅是这两颗无花果树,还有食堂后面大片的无花果林。这片无花果没有粗壮的主干,蓬蓬乱乱地胡乱蔓延,每年果子都随便结在低处,伸手可摘。在食堂吃饭搭配水果,但我们吃完饭还要到这里打个转摘个无花果吃。来这里认识或不认识的,重点都是彼此指引找到那个隐藏的熟果,这让人有一种“我们的”无花果树之感。果林边有五六只晒太阳的野猫,等我们用剩饭投食,或爱理不理,或谨慎怀疑。如此闲散的片刻,人似乎从工装下面脱离出来,做梦般恍惚发呆一瞬,不知魂游何处。无花果林消失之后,半生不熟的人们和猫群也隐于各处,像是从来未曾出现过。 山上的土质因为常年腐植,肥沃而蓬松。班上的同事大江竟萌出来要在楼顶养花的心思,这心思竟不是空想。于是几百斤的土一车车地拉回来,一点点地过筛,再一点点地运到五楼楼顶。再到现场去寻了废弃的塑料桶,中间一剖两半,约有一抱之粗,深深浅浅做了十来个容器,在里面种上了辣椒,丝瓜,小西红柿。大家一时都兴奋起来,往楼顶窜进窜出,甚至引了一根水线到楼顶,配置了晒水的大桶,竟还放置了一把小凳子。我们是轮番值班,交接浇水事宜,叮嘱大风大雨时,小花盆想着搬到屋里,凡此种种。但盆栽们只是勉强生长,没有精神。屋顶都是水泥,夏日暴晒,植物其实耐不住,秋天结疏疏落落的果子,也是尽力一场了。 后来班里的人一个一个退休走了,只剩三人。大江是其中之一,他痴爱钓鱼,在朋友圈里写“一丈青竹一丈线,一点猩红碧水间。一生垂钓何时休?一春去了一春还!”挥洒的畅意之下,却是身体大面积重度过敏,遍寻各地名医查不出病因,他即便用研究钓鱼的耐心与韧性来应付这场病,奈何三年来确诊不了只能服用激素控制症状。他说自己想得开,继续在班里养昙花,提醒花开去看,因为昙花一夜之间的端丽大气之美,很容易错失在实验室空无一人的寂寂黑夜之中。 班里去扔垃圾要经过一段山坡修整出来的路,路边长着很多酸枣枝和荆条,春末时空气里弥漫着微微清甜的香味。我和彤彤会在这条路上散一会步。春风从脸上、手臂上穿过,温而干,月亮大而圆地在装置上悬浮,一切显得那么安静而舒展。我们会说起很多久远的事,那些曾经因为不懂或者不解,我们错过的一些本该美好的日常,当时只道是寻常,后来才明白人生无数来不及好好体会便已错过。她父亲已过世多年,可一直在她心里的隐秘之处。这样的话,似乎在哪里说都不太合适。面对面正襟危坐着说,于我们都太重了,若是平常时分,并不容易张嘴——因为我们都惯于急着赶往下一刻。 偏偏此时最能感觉到天空疏朗,草木在旁,均都静静守候,默默无言,而这样的情形,我们的言语都离自己近一点,感觉得到另外一个人就在身旁。所谓无所求未必不可得,就是这样的时刻吧。 后来,彤彤调走了,酸枣和荆条都因为整修铲除干净,就连垃圾场也废弃不用。生命里的事,谁能给谁一个凭准呢。月亮仍旧在装置上悄然升起落下,春风仍旧年年来拂面,草木盛衰皆有其意,那些过去的才构成了人生,而未来将得到的和要失去的,早已经写好了,等我去经历和告别。面对未来,人和草木都是一样的。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#个上一篇下一篇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tanhuaa.com/pzth/8101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养拳四例
- 下一篇文章: 不同植物,一天当中开花时间不一样,真神奇